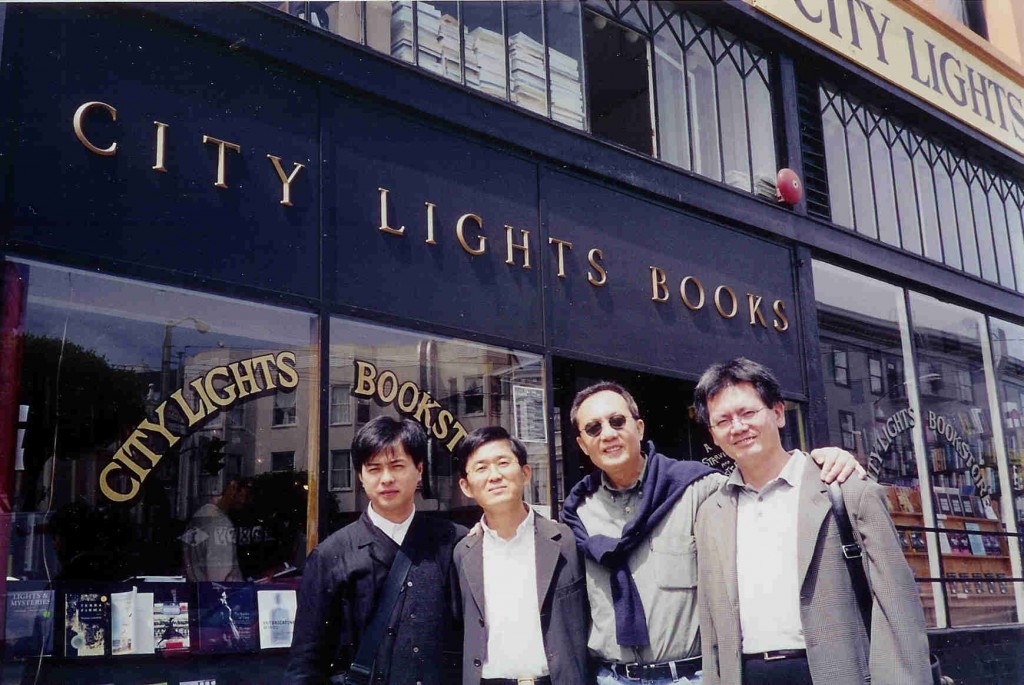報導文學 |
|||||
1、談研究領域 李鳳亮(以下簡稱“李”):我們談談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吧。我在做海外華人學者課題的時候,發現這一塊正日益受到重視。 張錯(以下簡稱“張”):我們這一代的,當然也有我的兄長輩的——李歐梵、葉維廉、楊牧都比我大——都是外文係出來的,潤華跟我同輩。那個時代從台灣出來搞文學的,不超過十個人。而這十個人中,真正從中文係出來的很少。而從外文系回到中國文學來的,就有四個人。 李:海外批評家的知識背景差異很大,現在大陸也有一些學中文的出去,我注意到跟台灣學英文的不太一樣。 張:不一樣,基本功差別很大,尤其是國內出去的,我坦率一點說,這個不能比。港澳台出去的,不僅學的是繁體字,而且那個時代剛好是上一代的萎退,下一代的成長,比較注意古典傳統。儘管我們搞西方現代文學,跟鄉土文學也有一點關係,好像要回歸到所謂的鄉土,當然不是本土,那時候在台灣不能說是中國。我們很開放地接受西方的東西,但在思維里面迫切感覺到一種傳統的需要,認為中國傳統是不能丟掉的。可是有一些從中國大陸出來的新一代的學生,這一方面就沒有了。 李:王元化先生在其《九十年代反思錄》中,對“五四”作了深刻反思,也講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一種激進主義的東西,總認為新的比舊的好,現代的比傳統的好,其實不然。總體上覺得有點矯枉過正了。您的研究領域主要在哪幾個方面? 張:我近期的研究有三個領域。一是文化藝術研究,二是“前五四”文學,三是華文文學。 張:那我們先從華文文學研究談起吧。 張:我提倡海外華文文學,除了定義華文文學有它的獨自領域,尤其倡導“華語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但我又認為“海外華文文學”是一個本土的延伸,沒有本土,何來海外?海外和本土是一個延伸和互動的關係。在國外開會會碰到不少海外華僑作家,可是明眼一看,哪些是圈內的人,哪些是圈外的人,哪些在繼續跟國內文壇發生關係,一目了然。我剛好今天就有兩首詩發表在台灣《聯合文學》的6月號上,就文學創作來看,我何嘗離開過中國本土!你看我一年內在台灣發表的東西,在聯合副刊、自由時報、聯合文學,算是多的。這樣才能夠產生比較特殊的成分,就不能光說我是海外不思歸的作家。假如你說海外作家的定義就是描述海外的環境、風情、心理,那就找不到這一文學的基本特性和傳統。 李:我贊同您的意見。海外華文文學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不是一個單一概念。我理解至少有這樣兩層意思:一個是海外華文文學,再一個是中國新文學在海外,沿襲中國整個20世紀新文學在海外的思路。前一個已經研究得多了,後一個,講20世紀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延伸、拓展,做得還不是很多。包括關注海外華人學者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也是剛剛才起步。我近年的主要課題就是做這個。我稱之為“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海外視野”,認為放大了的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史應該包括像夏志清、李歐梵、您和王德威這樣的海外批評家。這其實已是一個事實,從近年來海內外批評界交流的日盛可以看得出來。 張:我也很奇怪,尤其從90年代開始,我回來的頻率非常高。除了華文文學,我關注的第二個領域是“前五四”文學。我覺得“五四”文學本身不可能是1919年開始的,它跟晚清文學的關係非常密切。李歐梵、王德威、唐小兵、劉禾他們都看得出來。這是一個很值得發掘的領域。王德威搞晚清文學,晚清跟民國的重疊非常強烈,明清的重疊也是這樣,明清的研究有時候也要聯繫在一起。李歐梵很早也說過,傳統與現在不能分得很清楚,他們也看到這個問題,可是很多學者進去研究時,只不過研究晚清小說、譴責小說而已,魯迅當然也說了幾下那些譴責小說而已。我警覺到這個問題,後來就把它推到鴉片戰爭,後來又覺得不可能是鴉片戰爭,應該是更前,我就推到1600年,利瑪竇來華,當然他不是第一個傳教士,可是他是第一個有代表性的傳教士,他一直到北京去,是個領袖,然後我才產生出基督教文明入華的研究,那隻是我一個片斷,是前面的一個部分,一直要做到基督新教入華,差不多才算完。目前我做到的是翻譯小說的誕生。 李:這涉及到整個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史。 張:對,其牽涉之廣,太大了。我現在考察“前五四”文學的時候,就牽涉到基督教文明,我這不是像朱維錚、黃一農等學者在研究宗教學、宗教文化學,我還是從文學的角度出發,因為現在文藝的研究已經拓展到其他的領域了。 李:畢竟要有一個宏深的背景。我上大學時候,有位老師開了一門中國現代文學思潮選修課,他先是推到晚清,還不過癮,然後往前推到晚明,跟我們講李贄,當時我們很多人還不理解。 張:李贄也見過利瑪竇,說利瑪竇“此非常人也”,李贄自己也不是常人呀。 李:近期由英國倫敦回來的趙毅衡先生也致力於此。趙先生用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去關心中西文化交流史,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學做的比較文學的博士。他更關注20世紀早期中國一些行走在中西之間的文化名人,《西出陽關》等幾本書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現象的。 張:這種交流當然不僅僅限於文學,還有各個方面的。 李:我想像您還有趙毅衡先生本身在國外,有優勢來研究這個,可能跟自身所處的這個交流的身份也有關。 張:我們這批人在做學問的時候,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英文叫做shopping around,就是你到處在尋找,我們也是在看在整個的學術領域裡面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搞,隱隱約約,或者不約而同,發現有些方面還沒有好好地處理,有點所謂英雄所見的,不約而同地想填補這方面的空白。趙先生不見得是在做文學方面的,就跟我做這個西學東來的題目一樣,不單純限定在文學的研究。 “前五四”我才做到翻譯小說,一條路走下來,在做“五四”時我還涉獵到,它不是過去所講的現實主義,而是自然主義,像魯迅的作品。我教本科生中國現代文學翻譯課的時候,那些外國學生常常問:老師,為什麼20世紀中國沒有一本快樂的小說?為什麼小說里中國人那麼苦?快樂的大概就只有是老舍的部分幽默作品,比較輕鬆,然而對社會諷刺亦入木三分;而沈從文、巴金、茅盾、魯迅、蕭軍、蕭紅等等,都沒有一個快樂的,沒有一個笑容。其實,他們在反映出生命在某種環境之下的掙扎和犧牲,那正是自然主義的真諦,因為自然主義強調在自然裡面人只是一個動物。那個時候為什麼自然主義那麼厲害,我覺得深受嚴復翻譯的進化論影響。魯迅看過嚴復的書,讀了以後才發現原來還有這麼一個人寫《天演論》出來了,他感受很深。我覺得《祝福》寫祥林嫂,完全是在描寫那個環境,不是人為的悲劇,而是人在悲劇的環境裡面產生的悲劇,他們要表現的東西不是人物,而是環境。沈從文也是一樣,如《蕭蕭》、《燈》,都是在反映那個時代背後的環境的悲劇,以及悲劇的過程。人只是自然裡面非常渺小,有時連名字都沒有。我還想往這裡面去探討,做完這個新小說,我還要寫林紓,說不定還要講王韜,然後我就處理這個自然主義文學的主題。李歐梵說是浪漫主義,我覺得不全是,我覺得除了浪漫主義還有一個自然主義的誕生。 李:李歐梵先生關注浪漫主義,可能是講一些作家受西方的影響更多,像徐志摩、郁達夫、“新感覺派”。 張:他還講到第一身述說的小說,就是在日本所謂的“私小說”,我的告白,我的懺悔,當然也有西方的。 李:這方面郁達夫非常明顯,比如《沉淪》、《春風沉醉的晚上》。 張:對,郁達夫本人日文非常好,他吸收西方的、日本的。說回做這個“前五四”文學的研究真的很辛苦,因為不止浩瀚廣博,而且經常踩到別人的專業領域。有時真的很想退回來。我那些朋友說,到外語學院算了,講講外國文學呀,開門課呀,但我不願意。我很想做這個事情,每次寫一章回就是一篇學術論文,就如一場戰爭,因為它牽涉到閱讀、思考、寫作、修改,還要遍覽別人的專業研究。這是一個“自討苦吃”的事情。但我不想就此放棄。 我的第三個領域是文化藝術研究,主要是對中國古代文物的觀念整理與研究。我主要領域在青銅和陶瓷。青銅實在太浩瀚淵博了,完全是走到藝術的另外更大的一個文史與考古領域。陶瓷這個領域也不簡單,然而非常迷人,那是另一個色彩與造型的美學世界。我是從文化史角度,來研究器物的出現。我要追問的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圖型話語?這就是我近年致力的一個新領域。 李:您本身有不少詠古代器物的詩作,應該說是創作和研究的一種相輔相成吧。 張:可以這樣說,但自已做器物研究學習很不易,除了讀書及請教專家,最初的時候是上網讀,看對器物的描述,文字在呈現它的視覺的效果,而不是用圖像,通過這樣一種視覺的文本去想像文物,很有意思。今年4月的時候,我還在台北的《故宮文物》月刊發表了一篇唐傳奇的《古鏡記》研究,也是一個文本視覺化或者視覺文本。在創作方面,我還有些組詩是有系列地談唐三彩或青銅鏡的,有時我還用散文描述我為什麼會寫這些東西;另外一本詩集《浪游者之歌》中也有很多寫陶瓷如宋代茶盞、什麼兔毫、油滴、鷓鴣等的詩歌。寫古物,當然不是藉詩還魂,而是藉器物來描述心情。這是一個文字的終端挑戰。人家跟我說這些詩中的故事都可以寫成一個小說,但我沒有辦法寫成小說,就如你做素描你就要把它描出來,我們應用文字的要把它說出來,這是很大的挑戰。我對視覺文化的研究,這方面的東西很多。這個月台灣的《聯合文學》月刊,就有我兩首詩—〈宋瓷兩首〉,通過詩來寫器皿。其中一首寫《定窯玉壺春》就是一個瓶子,一個酒瓶。裡面用的術語,假如是行內人的話都明白,為什麼定器碗盞芒口呢?就是它覆燒時在碗口邊留下了一圈沒有上釉的芒口,人們在碗盞口邊上加鑲了一道金或黃銅的箍邊。但是我寫玉壺春的造型,卻是把器物人物化了。 李:就是用詩歌的方法呈現它的意態和韻涵。 張:對,我現在每個月都給馬來西亞的雜誌寫一個文物鑑賞專欄,促進了我學術上文物的修養,另外在創作上也給我打開了另外一個領域,就是詠物詩。 李:其他詩人有這方面興趣可能也不會去寫,因為缺少這方面的學養,這東西不是一般人能觸摸的。有很多人,比如說玩古董的人,不會表達,看到這個藝術價值,就去收藏,但是不會通過藝術語言來表達。 張:這個非常重要,詩的挑戰就在於語言,就是你能用你的方法說出別人不能說出的話,它就是詩。 2、談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李:我在閱讀中發現,美國現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對中國大陸影響很大。像當代批評中十分重要的“重寫文學史”這樣一些命題,都與海外有著絲絲縷縷的聯繫。我想知道的是,像中國現代文學這樣一個學科,在美國經過夏志清先生,還有您以及下面一代人的努力,現在在美國的學科建制裡面達到一個什麼狀況? 張:美國大學裡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案與動向,似乎沒有態度明顯的一個擬訂,因為從結構主義起來以後,所有的學科都變成跨越,大家反而不用這種時間的分期去定義文學和文學研究了。比如李歐梵的“狐狸學派”就很廣,還有王德威,他早期時候是做晚清文學,唐小兵以前也是做梁啟超的,後來大家都不再用這種明確的分期。至於你所說的“中國現代文學”是有的,但並不像大陸限定得那麼清楚,又有當代又有現代,還有晚清、近代,美國沒有這些,有時甚至只分現代與前現代(pre-modern)的古代研究。 李:實際上大陸“重寫文學史”,打通這個現當代甚至晚清文學,正是受了國外學人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美國是否屬於漢學的一部分? 張:它應該是屬於漢學的一部分。漢學中有一派是社會科學的,還有很多是從歷史方面去研究的,比如說黃仁宇、史景遷,當然他們的歷史是用一種野史的方法來寫的,在國外還不是完全能接受,可是它們還是漢學的一部分,這種整理是從社會科學、歷史、文化等切入的,長期下來,形成了一個研究的傳統,對文學研究亦有影響。從前我在華盛頓大學念中國文學史,就是上面的漢學思路。通過當年的英文或者外語的雜誌來研究東方的東西。中國現代文學也屬於整個漢學,也有其自身的學科規範。 李:像我們談的海外現代文學批評家跟比較老一些的做詩學研究或者做傳統的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研究路線的差異還是很大的。 張:對,差異很大。沒有太多的互動和來往。只是你有時候參加大型學術會議時能碰面。每年3、4月份之間,都會有一個亞洲學會的年會;年底12月的時候還有一個MLA,美國語言學會的全國年會,亞洲研究只是裡面的一個部分。 李:大陸有學者認為,海外批評家尤其是一些年輕學者,好像有種雙面鏡像,就是他用英文寫的,跟用中文寫的給中國人寫的東西,好像是不太一樣。 張:的確是這樣。李歐梵先生講過一個雙重彼岸的問題,一方面他們是站在西方來看中國,另一方面他們還有一種心態,畢竟是華僑華人,到西方後,首先是站在中國看西方。 李: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中西批評交流中的“話語權力”關係問題。面對強勢話語的西方,該如何認同自己,是更貼近它,還是有意識地保持自我,這個問題現在頗為複雜。很多海外批評家在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做中國新時期的影像研究,比起文學研究,其中的口味、結論、方法更加西化。 張:確實存在你所說的情況。這裡面可能跟知識背景和年齡差異都有點關係。不知你注意到沒有,像我們這一代人,包括楊牧、歐梵、葉維廉在內,學術只是一方面,我們精神的至高追求還是在於創作,這是一種寄託。而現在中國大陸出來的學者基本上不是這樣。其實不需要創作,學術我也可以自我滿足。但批評本身對我們來說可能是我們謀生的一個手段。 李:還有更重要的精神寄託問題。 張:像李歐梵,已經到了從心所欲的境界,卻還不忘情創作。他搞了一個與張愛玲《傾城之戀》“互文”的《範柳原懺情錄》,還有新出的懸疑小說《東方獵手》,幾十年的壓抑他還是要搞創作,我也感到很奇怪。我跟他幾十年的朋友了,記得以前聶華苓在愛荷華大學搞一個“中國周末”,我朗誦了自己一首詩,歐梵站起來說很喜歡這首詩,說只可惜是用中文來寫,然後他就現場把我的詩歌翻譯成為英文讀出來。我發現有一些學者是非常尊重創作的人,有一些學者不是不尊重,而是說他沒有興趣。李歐梵一方面是他的壓抑,也想做一個創作者,另一方面他非常尊重創作者。 李:我在博士後報告中寫過2萬多字的李歐梵先生的專論,我就發現他很強烈地受到徐志摩、張愛玲這批浪漫作家的影響。一個人受研究對象的影響是很大的。 張:一定的。 李:我本人對他創作是很尊敬的。總體評價是另外一回事。 張:他那些是遊戲之作(笑)。 李:尤其是《範柳原懺情錄》的書後附錄了毛尖女士所作的《狡猾的故事——〈範柳原懺情錄〉座談紀要》,裡面讓米蘭•昆德拉、張愛玲、艾侖•雷乃、李歐梵、傅雷五人作跨時空的對談,明顯是一種後現代式的遊戲之筆。在李先生的學術著作裡面,就不再是一種遊戲,但是有跳躍性,有跌宕,一些意念常像火花一樣一閃。 張:回到學者、批評家的創作問題,那顯然不僅是一個學術行為,更是一種精神寄託。 李:聞一多很難說他是一個詩人還是一個學者?如果他不是一個詩人,那他作為一個學者也不是這樣一個學者;如果沒有他對楚辭的那種研究,他寫的詩又不是這個味道了。但現在我們年輕的學者似乎完全斷裂掉了。 張:我剛才說了,我們這一批從台灣出來的,大概不超過十個人,在美國教書的,做比較文學也做中國文學,可是十個有九個都是念外文系,變成我們的底子還是英美文學,還是外國文學。後來發現文學的觀念也不以國族來限定。我念完碩士以後(我碩士還是念英文系,拿的是英國文學的碩士,博士才是比較文學),就有一個選擇:念博士的時候,我在想我要念中國文學,還是英國文學呢?然後我就念了比較文學,這樣比較折衷一點。王潤華是我大學時的同班同學。可是他研究所念的是中國文學,所以他跟周策縱先生很好。我念英文係出身,總覺得有一些自己的東西捨不得拋棄,但我繼續念英文系的話,就很難了,所以後來乾脆就選了比較文學。剛好那時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有一批老先生還在東亞系,我的老師施友忠是福州人,後來到燕京大學念哲學系,他是馮友蘭的學生,可是馮友蘭只比他大三歲,他在福州時是在教會的環境裡面長大的,所以他外文的底子非常好。在燕京的時候,馮友蘭就跟他說,我這《中國哲學史》你要趕快翻譯了,你不翻譯別人就會翻成英文了。但是他沒有翻譯。結果馮友蘭這個書果然就被外國人翻了。施友忠先生是《文心雕龍》英文本的翻譯者,那個功夫是很大的。所以他在美國的漢學界就以《文心雕龍》這本書的翻譯奠定了他在整個漢學界的地位。 1939年施先生就在我現任職的南加州大學念了一個哲學系的博士。後來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時候,他就變成我的老師了。我博士畢業後又跑到他讀博士的南加州大學去教書,施先生退休到了洛杉磯,我們常常在一起。兩個人很有趣,一碰到南加州大學跟華盛頓大學打球賽的時候,我倆都不知道誰幫誰了。華盛頓是他教的學校,卻是我的母校;南加州是他的母校,卻是我教的學校,兩個都不曉得是幫誰好了。後來就無所謂了,誰贏我們都很高興。我那時候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讀博士,就是因為這幾位先生。一位叫衛德明(Hellmut Wilhelm),德國人,還有李方桂先生是語言學的,蕭公權先生是政治思想史的。我主要是跟衛德明和施友忠老師,衛在北大德文系教過書,是沈從文的好朋友,在北大的時候也是馮至的好朋友。馮至在德國留過學,是海德堡大學的博士,搞里爾克。早期我在華盛頓大學,70年代海峽兩岸的書幾乎都沒有來往,這位衛德明教授有很多沈從文、馮至給他的著作,我就從他那裡看到了很多馮先生的書,引起了我對馮至的興趣,所以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寫馮至的。 1981年我到北京找馮先生,大家見面都很親切了。我也去找馮友蘭先生,那個時候他還在燕南園,他還記得他的學生施友忠,變成我是他的徒孫了。 李:馮至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也算一個熱門了。 張:前幾天我見到《南方周末》的馬麗和她的先生朱子慶。朱子慶是搞詩歌研究的,他大學時候還寫何其芳呢,我就跟他說,這些老先生,如卞之琳、馮至、王辛笛、穆旦、袁可嘉、鄭敏、陳敬容,他們這一代有一個抒情的傳統在裡面,尤其是何其芳,他抓到了語言。當初新詩發展的時候,很多人尋找語言都沒有找到。小說好辦,包括魯迅他們抓白話也不是抓得很好,他們都是文白相間,你看他們搞翻譯小說的時候都有點亂。新文學的發展是否真的可以用白話取代文言文?我看不見得。從翻譯來看,林紓的一本《茶花女》就讓大家都感動了,可見新文學不能完全代替掉古文,而只能從古文裡面去演變。那個時候他們要打倒這個東西,所以斷裂掉了。外國的詩歌理論也常常會碰到這問題。比如美國有一本很重要的詩歌發展史《美國詩歌的延續》,是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一位教授寫的,作者主要指出在整個詩歌傳統裡面有哪些巨人。他認為詩歌發展是一種延續。當然美國祇有200多年的歷史,可是延續的東西並不是可以代替的東西。 李:您很強調傳統的力量。 張:對。越是這樣,我就越覺得,在新詩發展的語言裡面,傳統語言他們後來真的找到了。從傳統語言裡面產生了一種新的生命。它是從抒情詩裡面找出來的,從傳統裡面找出來的。 1978年以後,我們覺得這些老先生再不出來就沒有什麼機會了,於是就由聶華苓和我來組織。東岸差不多就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讓他們先到東岸來參觀,然後我們在西岸見面。那個時候北加州有許芥昱教授,他是搞當代文學的,編了很多書,他就在舊金山州立大學任教,這樣一路連下來,就很順利了。 李:這裡面有個問題,就是您剛才提到的,包括您在內的許多美國華裔學者、作家、批評家,並不只是自己寫作,而且還把國內包括大陸台灣的文學傳統向外面推介。這個工作國內學者不大好去做,包括跟美國的出版社、學術界交流不是很方便。我記得李歐梵先生在《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裡,也提到大概有一段時間,跟幾位先生把中國的小說翻譯到美國去。 張:就是在印第安納大學,跟葛浩文、劉紹銘他們。這個整理也是劃階段的。從五四新文學開始,一個短篇小說的發展編成了一本所謂的教科書。教科書是一本選集,是原本的翻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也出過一本《台灣現代詩歌選》,1987年出版,台灣也有中譯本《千曲之島:台灣現代詩選》。我們做這些事情,無形中就把這些觀念灌輸給外面,李歐梵、劉紹銘他們在做短篇小說的整理,詩歌方面我出了一本,聶華苓出了一本百花文學選集,變成我們都在翻譯作品,也在整理文學,因為在選集裡面你就要產生出你對文學整理的觀念。 李:對,選本實際上有您的一個標準,有選編者的研究評價在裡面。 張:是。我們負起翻譯的責任。從中國大陸出來的留學生,對台灣現代詩壇不了解。台灣學者、詩人對大陸詩人、學者的了解遠遠要超過大陸對台灣詩人、學者的了解。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大陸留學生在國內資訊不通,同時意識上也有某種抗拒,結果大陸的留學生出來,跟我唸書,念到現代詩歌發展,一到“五四”以後,就斷裂了。直到“朦朧詩”前面的這一段空白,不曉得如何去填。 李:對,要到台灣去找。 李:而那個時期恰好是台灣現代文學發展的時候。如果把台灣文學納入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進行考察,結論會很不一樣。 張:變成整個觀念都要重新整理。美國學者也是這樣,比如他的重點在大陸文學,台灣文學他不懂。林培瑞(Perry Link)當時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他凡是跟我談台灣現代文學的,就說,“張錯呀,這個是你的。讓你來談這個,我不懂。”我說:“老天呀,你這樣不行呀。”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我的中國性很強。可是從整個文學發展來看,這段台灣的文學是不能抹殺掉的。 李:所以後來國內一些學者提海外華文文學,從這個角度來看也是非常重要的。恰好是從語言文字這個角度入手,突破地域性比較封閉的一個視角。 張:我這次到暨南大學來,講眷村文學。當年國民黨60萬大軍,兵敗如山倒,不到一年全部撤到台灣來,然後有60萬到100萬的軍眷住在村子裡面,還有兩三百萬沒有逃回來,在台灣形成這樣一個異類的存在,這個比陳映真那個《將軍族》複雜得多了,那是另外一個角度。研究華文文學時,像眷村文學這些都要整理出來。到底定義在哪裡?何謂海外文學、何謂華文文學?何謂華文作家?何謂海外作家?還有我們這批從台灣出來、不斷在台灣出版(還加上在大陸出版的,因為我們在大陸要慢慢發展起來,讓人家知道我們寫的東西),這群人如何去處理?怎麼去類定?怎麼去演繹? 李:包括資料問題,實際上海外作家也好,批評家也好,他們的創作與研究與大陸作家、批評家很不一樣。目前是關注海外作家多一些,批評家談得少一些。有一部分批評家的著作在台灣出,大陸也不容易看到。但這種批評狀況客觀存在,你不可能忽視或者說迴避它。如何去解釋這個現象,觀點不一。有些人把它當作20世紀中國文學在海外,有的人把它當作受西方文學影響的海外學者、作家。其實這些批評家陣容的成員還在不斷地變化。 張:對,他們互相的化學作用是什麼?並不簡單是一個優劣的問題,並不是某某人寫得好與不好,而是說這個內涵,語言當然是華文,這是不容爭議的。 李:好多人都講過,在考察海外華文文學和華裔文學的時候,過去的人總是講怎樣去界定它的藝術價值,實際上這種創作現象包含了幾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文學的審美層面,這個是共通的;但另外還有一種特殊性就是作家的身份,作家不是在國內寫這些東西,他是在海外,那麼身份就變得很重要,他自己也會有這種心態。 張:對。現在研究我們海外華人作家和學者的擔子落到了你們身上,變成了要通過第三者用超然客觀的學術立場來把這個身份、心態整理出來。我們這些在海外的都還是當事人,你們相對超然的審視對我們很重要。 李:實際上華人作家、學者間心態的分歧比較大。像您跟李歐梵先生基本上是同齡人,但在文化立場上差異其實不小,是吧? 張:對,你可以看得出來。 李:我過去寫過李歐梵先生的專論,這樣對照著來看更見問題的複雜性。 張:應該這樣來說,海外華人寫作者的類型是不需要統一的。它代表了很多種複雜的心態,有重疊,也有分歧,問題是怎麼去把他們歸類,就等於說先從一個大的變成一個中的,中的變成一個小的。目前不是說華人作家有幾百人嗎?這幾百人裡一定可以分得出來。 李:這個跟美國作家區別很大。 張:對。我們不是美國作家,但我們應該歸在哪裡呢?台灣每個月我都有東西發表,我從沒離開過,可是這個向心跟離心的互動,非常的強烈,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化學作用在那裡呢,那就是選擇的問題了。 李:這個張力也好,問題也好,恰好就在此之間,如果您靜止在那裡沒有互動或者您沒有出去,這個問題就不會出現。您的古典傾向非常強,您也自認為民族主義傾向比較強,其實也不是說您真地想回到古典裡面去,實際上您用了很多新的眼光去看,這裡面跟在國外受到的這種訓練、熏陶、影響很有關係。 張:對,比如一個杯子,它永遠是一個杯子,看你從什麼角度切入,放冷、暖、冰水、茶或酒、一個文物乃至任何一個風景也是這樣。你用什麼心情、角度、觀點,怎樣敘述、演繹,每個人都不一樣,這就牽涉到他的思維。我用古典,並不是剽竊古人的原貌,其實模仿說本身並不是在模仿,而是在重新演繹。一些題材,古代很多人都寫過,可是你演繹的精神不一樣,唐代的邊塞詩跟古代的樂府就不一樣。你在當代當然也可以寫。 3、談海外華人批評家 李:在承認個性差異的前提下,我目前也在從一個較宏觀的角度,去考察海外批評家這個群體在研究取向、方法觀念上有沒有共通的方面,比如您覺得在美國受到的學科規訓是不是一個主要的方面? 張:這個是有的。西方的理性意識很強,也就是說你在學術整理的時候是非常理性的,在研究過程中絕對是個理性的動物。可是就創作來說的話,那就不一樣。像我跟歐梵的差別就反映了這一點,也可能是他創作上的壓抑感太大了,非得要去創作去發洩他這幾十年來的慾望。而從前他在進行理性的研究的時候,是分得很清的。另外,研究的取向跟個性也有點關係。 李:海外批評家的內部差異可能有很多方面,國內就有很多種分法,比如說年齡的差異,這個算不算?過去有人把你們去美國的這些學者分為三代,我不知道這樣分法是否正確? 張:我也不知道這樣分法成不成功,但覺得有些道理。像白先勇他們,我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都是把他們當作大哥來看待的,就等於說這一批是我的大哥,也包括歐梵。為什麼呢?因為我在台灣念大學的時候,他們已經來美國在研究所讀書并快要教書了;在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他們已經可以做我老師了。 李:那從一個大的框架來看,您和上面這些同輩人跟他們相比,夏志清、夏濟安先生應該算是第一代。 張:這就很清楚。 李:第二代就是您這一批。 張:對,中生代。六七十年代出去的。 李:然後第三代就是八十年代出去的。 張:對,後來從中國出來的比較多,像唐小兵他們。你說詹姆遜到中國大陸是在哪一年? 李:最早來1985年來北大,作《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的講演,唐小兵先生是該書的中譯者。 張:這批出來的是新的一批。 李:後來大陸去美國的比較多了。 張:對。我們這一批跟中國的感情非常的濃厚啊。 李:除了年齡差異,還有一個是地區差異。您剛才講到台灣出去的多是外文系的,大陸後來出去的主要也是外文系的。但是我在閱讀中發現台灣出去的跟大陸出去的,所接受的傳統訓練不一樣。當然李歐梵先生他自己講,說自己的古典功底不是很深厚,以至成了很大一塊心病。這是他自己謙虛。但是大陸的80年代出去的我感覺更加西化,尤其跟白先勇、葉維廉、王潤華、李歐梵等先生和您相比。 張:我們那一輩人對於傳統的確非常注意,包括歐梵其實也沒有脫離。像我跟王潤華是大學外文系的同班同學,後來他走到了中國文學,可是我們在大學的外文系或者英語系,正當來說叫西語系,都去聽中文系的課呀。這是一種自發的行為,沒有任何人逼迫,可是我們覺得有這個需求,要回到傳統裡面去。這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大二大三這兩年要學生自動去旁聽或者去修這門課很不容易,因為本科已經有很多學分要修了,還有什麼選修課心理學呀什麼的,要我們跑到中文系去修這門課,完全是自己的渴望。我這個渴望是很強烈的。我們這批,像白先勇,他何時離開過傳統?他現在搞崑曲的時候,何時離開呢?到頭來搞了一大圈還是搞到最傳統的東西。 李:有個說法可能比較敏感,李歐梵先生回香港的時候,民間有一種說法,說在美國做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始終進不了學科建制的主流;既然進不了主流,還不如回到占主流的地方去談這個東西。 張:也有點道理。在美國,從助理教授升為副教授,從副教授升為正教授,審查過程是蠻嚴格的。首先要求你必須有一些著作,包括英文的著作,同時英文著作的出版社也很重要,以大學的出版社為主。美國大學出版社有非常嚴格的審查制度,他要把你的稿件送到外面去,取得兩到三個專家的閱讀評語,他才來做一個決定,要你按照評語去修改,你答應了他才寄合約給你。我們當初的時候還是掉到那個體制裡面去,還是規規矩矩按照那個體制去做。我最早的英文著作就是研究馮至的,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第二本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的,當然我還有其他一些研究中國文學的英文著作。比如說當時的比較文學最喜歡用中西比較,可是那個時候我發現可以變成亞洲的比較,像中日韓的比較,因為他們的共性還強於中西,所以又出了一些中文的著作,包括在上海三聯出的《批評的約會》。 李:現在國內的比較文學研究更主流的,還是中西比較,這三四屆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年會都是如此。東方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內部包括中日韓的也有,但是並不占主流。 張:這裡面有一個問題可能是語言問題,因為現在外語學習以英文為主,可是假如你靠翻譯,中日韓你要精通三國語言,比較困難。我有一點你說取巧也好,幸運也好,我抓到一點用漢語比較多的,日本的《雨月物語》不是漢語的,可是韓國有一本《金鰲新話》就是用漢語寫的,它是模仿由中國傳到韓國的《剪燈新話》所寫的鬼故事,然後再傳到日本去。上田秋成據此寫了《雨月物語》,這個跟中國的《剪燈新話》是絕對有關係的,有很多重疊, 李:也就是中日韓同類型的文學的比較。 張:日本的俳句、和歌,他們跟中國詩歌的意象、格律形式都有一些關係。當初我們都在美國這個體制裡面,要按照西方的要求去做。可是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階段可以不理會它了,我現在做華文文學就用漢語來寫作。 李:這裡面涉及到美國大學系科設置的問題。美國大學東亞系裡,中文學科與日文學科哪個強些? 張:都有,都很強,像我們東亞系,它有三大塊,中日韓,韓是比較弱、比較小的,而且它受漢文學的影響很大,它脫離不了漢語。三大塊裡面,真正的重點還是中日兩方面。日本的現代文學不得了。像現在的動漫、宮崎駿這些在新的大眾傳媒或者說通俗文學、大眾文化里面,其影響、本身的地位無可否認。他們在這方面做翻譯的學者也很好,懂日語的美國人也很棒。像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能拿諾貝爾文學獎,都是因為有非常好的翻譯。 李:剛才您講台灣的學者了解大陸,比大陸的學者了解台灣多得多。其實我感覺美國的學者跟我們中國人,應該是我們了解他們多一點。 張:對。 李:厄爾•邁納(Earl Miner)的《比較詩學》,他主要還是拿日本做例子,提到中國的很少,他本人是研究日本宮廷詩的。美國的比較文學系跟東亞係好像互相重合的,是不是人也互相重合呢? 張:沒有。他們喜歡跨學科,人員聘用上也是如此。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因為比較文學也需要一些亞洲的成分,遂產生了中西文學比較等需求,東亞系的人常常也被合聘到比較文學系授課。像我就是兩個系合聘,一個學期要教兩門課:一科是在比較文學系,一科是在中文系,也就是東亞系。國內留學生出來,原來念外文系的大部分都是申請比較文學,念中文系的就申請東亞系。 李:東亞系本身來說在美國來講是一個區域研究? 張:對。 李:那比較文學就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 張:對,但比較文學同時也在演變。它目前正變成所謂精英的一個學科,現在已經有點像文學系,因為它更多地從理論出發,不再作國別的比較了。 李:接著上面的問題:海外華人學者用比較新的視野或者方法反過來研究中國文學問題,國內學術界對此也有不同看法,像李歐梵先生、王德威、劉禾等先生的一些文章在國內都曾引起過不小的爭論。比如有學者認為海外華人批評家有重理論、輕材料、缺少整體文學史觀等傾向,形成了一種浮泛的學風;還有學者認為由於方法比較新穎,引起我們過去某種結論的變化,但過於強調方法、強調理論的投射,反而忽視了研究的對象。不知您如何看待? 張:對,有點本末倒置了。你看得很準,這種批評也有一定的正確性,等於說現在國內批評界已經到了可以負擔獨立的思考,對國外學術超越的再批評,外來的和尚不見得會念經。 李:但是反過來他們的觀點方法對國內的影響衝擊很大,我認為姑且不論結論如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識立場,包括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為什麼跟國內的差異那麼大,也有個立場、方法問題。但是恰好是這種立場和方法,是可以給我們以啟發性思考的,只要你能冷靜對待這個東西。 張:還有就是像我們這一代人,深受新批評的影響,我真的是吃新批評的奶水長大的。六七十年代,恰是美國新批評最盛的時候,我的整個方法論是從新批評那兒演變過來的,如結構主義什麼的,我對文本的敏感、注視超越了其他的一切。 李:從文本、從對象本身出發。 張:不錯。不是用理論來套。現在研究生在定學術論文題目的時候,都感到很困難,經常問,老師我們都不曉得寫什麼好。我說你不要問我,你先把文本定了再說。你找個文本來給我看看,你不要拿理論來套,否則你的理論都站不住腳。 李:就如兩張皮貼上去,根本不合。國內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就曾有過這個問題。我跟他們說,天底下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你隨便拿些境外的理論術語來貼,什麼漂泊呀,尋根呀,離散呀,我說對像很複雜,你要知道他是種什麼樣的漂泊,是流放呢,還是自我放逐,這個很複雜。我上次看到一部電影叫《時差七小時》,反映的是作者妞妞自己在英國一個貴族學校留學的經歷。英國貴族學校是什麼概念,大家都清楚。所以作為一代新移民,妞妞們根本沒有郁達夫,也沒有80年代留學生們那種自卑消沉的心態。那個時候的窮學生跑到國外去留學,千呼萬喚祖國你何時能強大起來,而新一代移民大多有較好的家庭經濟實力,根本不會去想這個問題。從這樣的新移民文學裡面,我們能找出漂泊、離散嗎?真地不能用一個理論簡單概括它。我覺得目前國內批判或者反思海外年輕學者的做法,對我們很有意義:他們好的方面對我們有意義,他們做得不好的對我們也有意義,因為目前國內也處於這種狀況——比較注重理論,注重方法論,文本變得不重要了,變成我說話不是一個根據,而是一個跳板,去講我想講的其他東西。 張:而且他經常不知道自己想講什麼,老是用人家的話,說這個是雅各布森的,那個是福柯的,但卻不知道自己想要說什麼。他認為福柯說的就是對的,我有時候跟牧師吵架就是這樣,他說這是聖經講的,我說你也講出個原因給我吧,你不能說這個就是對的吧。我知道這是神的話,可是你總也得詮釋出來吧,按照這樣,所有的那些西方批評家都是眾神了?那你自己變成第幾等的公民呀? 李:海外的方法論的確非常新進。我們80年代以來的理論都是從海外傳來的,很多就是由海外華人批評家介紹的。我看到的第一篇有關昆德拉的重要文章就是李歐梵先生寫的,發表在《外國文學研究》1985年第4期上,是一種比較文學的做法,作昆德拉和馬爾克斯的比較,還有與《紅樓夢》、張愛玲的比較,視野開闊,非常有新意,而且方法也是新的。但是這種肯定與對海外學者的反思爭議是兩碼事,後者眼下不失為一種警醒,因為國內跟的實在太快了。 張:我們反過來說,儘管我們強調文本,可是理論也不是不可以講的,只是要視事而定。比如我講到幻怪小說,那我就會用托多羅夫的幻怪理論,然後再從他那裡出發,我很想將來能在國內密集地開這門課,不用一個月,就用一個禮拜到十天的話,研究生先把我開出的書單都念好,然後就幾個重點來討論,效果應該會非常好。因為西方的這些理論儘管沒有牽涉到東方的作品,但對我們理解中國的文本也會有益,比如從魏晉志怪小說一直到唐傳奇,中國這樣的作品很多。 李:對海外華人批評家,我其實很矛盾。一方面像有些人所說的,他們的理論意識強,方法論色彩重,值得我們警醒;另一方面又要肯定他們對中國文學批評現代性的推進意義,包括方法觀念上的更新,還有他們本身作為批評個案的研究價值。其實不能將他們簡單理解為西方理論的執行者,實際上在用的過程中他們有很多獨立的思考,體現出西方理論中國化的一個過程,這個時候海外華人批評家作為理論中介和批評個案的意義就十分突出了。 張:我的《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有一個後記,說這是我念大學外文系又在外文系教書的一張卷子,並沒有白念。這本手冊是對西方一些文學批評術語所作的一種清理,女性主義、新女性主義、性別研究等等都有。因為國內對西洋文學批評及術語的譯介,有時比讀原著還困難,就是說還沒有把人家的東西吃透。做這本書主要是想在國內提起這種風氣,一種學術研究的認真態度,那樣也許就能夠面對世界了。我們現在只能接受世界,不能面對世界。人家說什麼,我們就听什麼,這是不行的。這方面咱們的基本功還沒做起來呢。 李:您提這個問題恰好引起我的感想,這幾年來,國內的學術會議都會談到西方概念、術語的內涵、規範及使用問題,感到應該把一些基本概念釐清,像韋勒克做《批評的概念》那樣,有個“概念史”,了解每個概念的來龍去脈,概念到底從哪裡來?在不同的語言中它各自的意思是什麼?在歷朝歷代包括現在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些都應該講清楚,不能憑空去用它。 張:對,不能憑空。韋勒克是從布拉格學派那邊過來的,布拉格學派又從雅各布森那邊過來,雅各布森所在的俄國形式主義尤其註重對語言的演繹。當然對理論也有誤讀,可是在布魯姆那裡,誤讀主要是講作者不要受到前人的影響,要從傳統裡掙脫出來。國內要加強對西方文學理論一手資料的收集工作,必須要有系統地買書。可能我們沒有辦法跟得那麼緊,可是西方經典的東西必須要有。書跟雜誌不一樣,你訂很多外文雜誌,如果學術閱讀的程度不高,就是白讀,讀不懂了他也懶得再翻。可是書呢,有基本功那些東西,就像我《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所列的參考書,你們都可以買,這是一個基本資料。 (時間:2006年6月2日、18日, 地點:廣州•暨南大學)
|
|||||
|
|